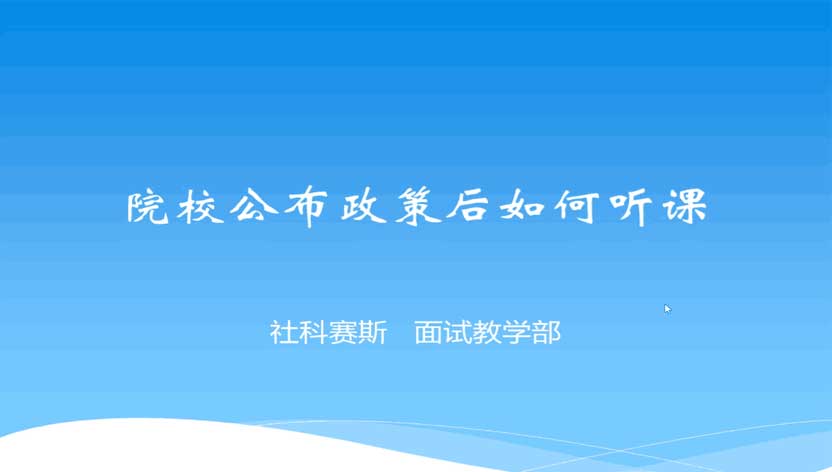2025MBA報考測評申請中......
說明:您只需填寫姓名和電話即可免費預約!也可以通過撥打熱線免費預約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最短時間內給予您活動安排回復。
導讀: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是對全球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利用,但依靠粗放式的資本并購,以及只是單向度地將海外技術拿回來,而不對別國市場提供就業崗位、進行技術反哺,會讓中國企業的海外形象受損,也會影響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布局。
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規模化,與其最終獲得的收益不相匹配。
先看規模。根據美國華盛頓兩大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在1月共同發布中國海外投資情況最新報告:2016年,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增長將近50%,達到大約1750億美元,刷新歷史紀錄。該報告還指出,在這股對外投資浪潮中,美國市場繼續位居榜首,成為最受中國企業青睞的海外投資目的地,投資規模超過500億美元。 而根據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此前表示,僅2016年前9個月內,中國企業共實施海外并購項目521個,實際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涉及67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并購金額544.4億美元。這樣看來,有關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規模化的數據,中外統計的數據基本接近。
然而,在如此之大的海外擴張中,中國企業到底收益如何呢?根據普華永道相關統計,至今為止,有超過50%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都不成功,普華永道的結論和商務部的相關報告也基本相似,在商務部最新的統計中國企業的海外項目中,只有13% 處于盈利可觀狀態,而63%則處于非盈利或虧損。 一邊是海外規模持續擴張,一邊是收益慘淡,中國企業的海外步伐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又將怎樣重新調整思路和戰略?
海外戰略,主打“買資產”
大部分中國企業制定海外戰略主要集中在兩個方向:第一、以企業全球化為目標,通過對海外資產并購方式來實現;第二、以“技術引進”為目標,通過對海外資產并購之后,再引進先進產品、技術、商業模式及管理體系,最終在國內進行落地實現。比較兩者,后者更為廣泛。
根據以往歷史經驗, “技術引進”主要有四種方式:一是外資和我們共同生產,用中國的市場換技術;第二是外資企業直接來中國投資;第三是我們向國外買技術;第四是中國企業買了國外企業,再將技術轉過來。相比前三種方式,透過直接向海外企業的并購,容易在短時間內更快速、更全面地掌握海外技術,因此成了當下很多中國企業的行動選項。
從美的收購德國機器人企業KUKA集團的案例中就可以看出,對于美的,KUKA的核心優勢在于機器人綜合制造實力強、下游應用經驗豐富,在美的要約收購KUKA的報告書中,就直接提到美的可憑 借KUKA在工業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領域的技術優勢,提升公司生產效率,推動公司制造升級。這也是美的積極收購庫卡的因素之一。
中國目前已由國際資本的凈進口國轉變為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股獨特的中國力量,并在投資界出現了“Buy what china buys(中國買什么,你就買什么)”的投資現象。中國的投資,初從以央企為主的能源類企業購買能源資產,投資遍布中亞、中東、北非、南部非洲、拉美等地,先后修建了連通中俄的北部、中哈的西部、中緬的西南部等輸油管道。并在澳洲、拉美、非洲投資購買鐵銅礦等資產,豐富了中國的資源供給。
從2016年海外投資并購呈現的特點來看,國有企業依然占投資主體,統計數據表明,地方國企占48.6%,央企占27.6%,國有企業在海外形成的資產仍在國資委監管下。海外優質的戰略性資產或重要的資源類資產,有利于提高中國國有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助力國內經濟轉型升級。
但是,隨著中國企業大規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資事件也越來越多。
普華永道認為,有超過50%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都不成功, 而在商務部最新的統計中國企業的海外項目中,只有13% 處于盈利可觀狀態, 而63%則處于非盈利或虧損。
“買買買”,阻力正在增多
“賺快錢、炒短線、盲目追逐高利潤的思維主導著企業的投資行為,總是把別人的危機當作時機。”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稱,所謂“抄底”,這是像索羅斯這樣玩金融的資本巨鱷玩的投機游戲,而任何一個干實業的企業都不應該有這種投機思維及心理。 自2015年年中以來,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擬議海外并購告吹—究其原因多數是因為各國政府日益擔憂安全和競爭問題。
日前,德國政府剛剛撤銷了我國對德國芯片 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6.7億歐元擬議收 購的批準,原因是收到了“先前未知的安全相關信息”。此后不久又宣布將對歐司朗的子公司被賣給中國進行審查。 在美國,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核通常起著關鍵作用,安全審查的重點是“關鍵資源”與“關鍵性行業”。該委員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在所有海外投資者中,中國投資者主導的交易仍然是CFIUS最主要的審查對象。除了CFIUS這類掌握安全審查的機構外,還有諸如反壟斷等機構會對并購交易是否成功起到作用。
除歐美之外,最近澳大利亞對中國企業收購澳企,也出現了審查和否決的情況。中國在全球投資的擴展速度已經在澳大利亞引起了擔憂,比如,澳大利亞社會上存在對“農場變賣”和利潤轉移到海外的擔憂。澳大利亞同樣有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 會(FIRB),使外企對澳大利亞企業的并購會變得高度政治化, 因為澳大利亞財長具有自由裁量權,可以以國家利益為由阻止若干交易。
“七問”中國企業海外戰略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律、文化以及市場等風險之外,今后要更加重視政治風險。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帶來門戶開放與抄底的機遇,我們中國企業需要把握這樣的機遇。但是在把握這樣機遇的同時,中國企業又需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冒進翻車的風險。”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貿研究部研究員梅新育提醒投資者。
2017年是全球政治超級特殊的年份,部分國家政權變更正在加大當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戰亂風險。即使是從經濟方面看,新世紀以來這10多年,除了中國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其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初級產品產業增長所驅動的。這種初級產品產業增長所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熊市到來時會面臨轉折。
不過,這并非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就要停止,而是需要重新思考走出去的戰略和方式。從《經理人》理解的角度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沒有錯,也是對全球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利用,但依靠粗放式的資本并購,以及只是單向度的將海外技術拿回來,而不對別國市場提供就業崗位、進行技術反哺等,勢必會讓中國企業的海外形象受損,也會影響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布局。
為此,《經理人》調取了部分在海外成功的中國企業案例,試圖給中國企業實施海外戰略進行總結,然而在梳理、總結之中,我們最終唯一的選案是華為,我們發現,這家中國企業是眾多走出去的企業中,難得的一家不依靠資本輸出而實現國際化的企業 (詳見本期《華為國際化熵變史》。尤其是該企業還借用物理學的“熵定律”,轉為其跨國戰略管理思維。因此,我們就華為的歷史經驗,給中國企業實施海外戰略,總結了一個“七問”的問題:
第一問:海外戰略的理由是什么?企業需要問清自己—實施海外戰略是出于市場原因、政治原因、金融原因、戰略原因、資本原因?是沒有原因,還是都有這些方面的原因?
第二問,在戰略目標、戰略理由制定之后,如何鎖定戰略目標?在戰略目標鎖定過程之中,是否了解戰略內容、內外部的資源以及供應商?在戰略實施過程中,是主動出擊還是消極被動等待?
第三問,對方市場能讓我們得到什么?是否達到了市場準入標準?自己是否有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管理知識、品牌效 應?
第四問,有沒有事前做盡職調查?盡職調查分兩部分,一是財務部分,二是非財務部分。其中,非財務部分的當地的法律環境、企業的文化環境、利益相關方的特質和特點,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勞工問題、工會問題等細節,是否完全掌握信息?
第五問,如何接觸海外市場?是否具備和了解當地市場的要素、市場運營的整個流程,包括自己的團隊組建、要約問題的設計、相關的法務,以及進入海外市場之后的管理和運營等。
第六問,是否具有雙贏?如果在海外戰略中,只想自己獲得最大的利益,不對海外、合協作伙伴留有余地,不讓對方得到任何好處,那么就算進入當地市場,最終的結局也會遭到惡意競爭,甚至當地企業動用法律手段對我們進行制約。
第七問,在海外成功的標準是什么?什么是成功的實踐?如何評價這個海外戰略是否成功?是指銷售額,還是市場份額、產品創新、市盈率、利潤或是資本回報率?這些問題都要思考。
“七問”只是核心問題,不涵蓋中國企業海外戰略遇到的所有問題。問題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一個企業一定要有健康的國際思維,有清晰的戰略目標和明晰的企業經營文化和價值觀,這樣,我們企業在海外經營才會取得更高的成就。